第一章:愚蠢之岛
咸腥的海风,如同岛上永恒不变的叹息,裹挟着海藻腐烂的湿冷气息,穿透薄薄的木窗缝隙,钻进阿加普的鼻腔。这味道浸透了岛上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块礁石、每一个毛孔。他站在自己小屋的窗前,目光越过低矮、歪斜的茅草屋顶,投向那片将小岛死死箍住、望不到边际的铅灰色海洋。数十海里外,是模糊的大陆轮廓,一个只在传说和偶尔的商船帆影中存在的“文明世界”。在这里,时间仿佛被海水泡得发胀、凝滞不前。
北大陆边缘的这座弹丸小岛,是世界的弃儿,也是愚昧的温床。阿加普对此深信不疑。四面环海的牢笼,阻隔了知识的风,只留下闭塞的盐碱和世代相传的愚蠢在空气中发酵。岛民们像礁石上的藤壶,固执地附着于贫瘠的土地,重复着祖先留下的、早已失去意义的劳作和仪式。他们的思想如同岛上的土壤,浅薄而贫瘠,稍微深挖一点,就能碰到坚硬、愚钝的岩层。
“蠢货。”阿加普低声吐出这个词,舌尖尝到一丝苦涩的轻蔑。这个词,是他对这个村庄,对这些所谓“大人”最精准的注脚。当然,除了他自己。他,阿加普,是这座愚者之岛上唯一清醒的囚徒。
他从小便洞悉了这些庸碌之辈的内心。那些脸上刻满风霜皱纹的大人们,弯下腰,挤出虚伪的笑容与他说话时,他们想要的从来不是倾听一个孩子的想法。他们只想听到自己陈旧观点的回音,得到几句廉价的恭维,就像给一头拉磨的驴子喂一把干草。阿加普早已谙熟此道。他只需垂下眼帘,模仿着他们期望的“乖巧”,重复他们话尾的几个词,再适时地、用恰到好处的天真语气加上一句“您懂得真多!”或“您说得太对了!”,便能轻易点燃他们眼中那点可怜的自得之火,看他们瞬间飘飘然,仿佛自己真成了智慧的化身。这拙劣的把戏让他作呕,也让他确信了自己的判断——岛上弥漫的愚蠢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瘟疫。
“厌蠢症……”阿加普的指尖无意识地抠着粗糙的窗棂,“如果真有这种病,我大概已经病入膏肓,无药可医了。”他厌恶这个散发着鱼腥和愚钝气息的村子,更厌恶构成它的每一个蠢人。而在这些蠢人构成的恶心图景中,有一个污点最为刺眼,最为纯粹,也最令他生理性地反胃——那就是诺德。
诺德是个傻子。这不是阿加普出于主观厌恶的贬损,而是客观的、生理上的事实,是岛上所有活物(包括那些不太聪明的狗)都心照不宣的共识。关于诺德的来历,是村妇们在织补渔网时永不厌倦的谈资:他的母亲亚里沙,是港口边那间散发着廉价脂粉和汗臭味的妓院里,一个早已过了“花期”的妓女。在一群虽不漂亮但至少年轻的女人中,三十好几的亚里沙格外扎眼。她赖以生存的优势,是“价格低廉”。就在这日复一日的“忙碌”中,亚里沙的肚子里意外地揣上了诺德。这意外的“馈赠”让她立刻失去了糊口的营生。至于孩子的父亲?村人们会带着猥琐而嫌恶的表情告诉你:“谁知道呢?也许是妓院上上下下所有男人的份儿都掺和进去了吧。”亚里沙对这突如其来的生命充满了憎恨,视其为恶魔的诅咒,害她丢了饭碗。她疯狂地祈求教堂的神父赐予圣水,企图用这“神圣”的液体洗刷掉腹中的“污秽”。结果,不言而喻。
诺德降生的那一刻就异于常人。接生的村医狠命地抽打他青紫的小屁股,直到那团软肉红肿不堪,婴儿却只是发出几声微弱、断断续续的抽噎,而非应有的嘹亮啼哭。他像一团没有生气的肉。随着时间推移,当其他孩子开始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,诺德的眼神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迷雾,反应迟钝,口水时常不受控制地从歪斜的嘴角淌下。村民们窃窃私语,笃定地认为这是不祥之兆,是连圣水都无法完全净化的诅咒在他体内扎根。阿加普对此嗤之以鼻。什么诅咒?不过是单纯地遗传了他那愚蠢母亲的劣质血脉罢了!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诺德的愚蠢似乎堵住了他的嘴——他极少说话,即使开口,也只能发出含混不清、意义不明的咿呀之声,像破损风箱的嘶鸣,倒不至于用愚蠢的言语去污染外界的空气。这或许是他对这个世界仅存的、微不足道的“善意”。
村里的孩子们,在大人有意无意的默许下,将欺凌诺德视为理所当然的娱乐。他们朝他扔泥巴,抢走他手里任何看起来像食物的东西,模仿他蹒跚的步态和扭曲的表情,发出刺耳的哄笑。诺德通常只是茫然地站着,或者迟钝地试图躲避,那双空洞的眼睛里映不出愤怒或悲伤,只有一片混沌的空白。
阿加普从不参与这种低级的“游戏”。并非出于怜悯,而是源于一种极致的轻蔑和厌恶。在他眼中,诺德甚至不值得他亲自去踩一脚。
记忆中最清晰的一幕,发生在某个同样弥漫着咸腥气息的午后。阿加普正沿着通往海边的小径快步行走,想尽快远离村子的喧嚣。就在路边一块布满苔藓的岩石旁,他看到了那个令人不悦的身影。
诺德蹲在那里,像个专注的鼹鼠,双手在泥土和碎石中扒拉着。他的裤腿沾满泥浆,头发纠结成一团。他似乎发现了什么“珍宝”,小心翼翼地捧起一小堆东西——不过是几块形状怪异、沾满污泥的破石头和几片在阳光下微微发亮的贝壳碎片。
看到阿加普走近,诺德浑浊的眼睛里似乎亮起一丝微弱的光。他笨拙地站起身,趔趄着挡住阿加普的路,将那捧“珍宝”高高举起,伸到阿加普面前。喉咙里发出嗬嗬的、努力想表达什么的声音,最后挤出一个含糊不清但能勉强分辨的词:“宝…石…” 接着,他用沾满泥污的手指,急切地指向阿加普口袋里露出半截的、用油纸包裹的硬面包(那是阿加普准备带到海边礁石上独自享用的午餐),“换…换…吃…”
一股强烈的、几乎要冲破理智堤坝的怒火瞬间席卷了阿加普。看着那张挂着痴傻笑容、沾着口水和污泥的脸,看着那双捧着垃圾如同捧着稀世珍宝的手伸向自己珍贵的食物,阿加普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般的恶心。他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,一股暴戾的冲动直冲头顶——他想一脚狠狠踹在那佝偻的腰腹上,把这团碍眼的、散发着愚蠢气息的垃圾踹翻在地,再踏上几脚,碾进这肮脏的泥土里!
他的拳头在身侧紧握,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。然而,就在那股戾气即将化为行动的前一秒,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,如同兜头浇下的一盆冰水:“别动。不值得。”
他深吸了一口带着海腥味的空气,强行压下翻腾的怒火和厌恶。他微微抬起下巴,眼神如同掠过路边的垃圾一样掠过诺德和他的“宝石”,里面没有愤怒,只有一种冻结一切的、极致的轻蔑。他甚至懒得开口呵斥,只是像避开一滩秽物般,侧身从诺德身边绕过,脚步没有丝毫停顿,径直向前走去。仿佛刚刚挡路的,不过是一条对着垃圾堆呜咽的、不值得多看一眼的野狗。
身后传来诺德失望而困惑的咿呀声,很快被海风吹散。
应付神父和识字学校的先生们,对阿加普而言,比应付诺德还要简单,简直如同孩童的游戏。他们和那些村民没什么本质区别,只是披上了一层更精致的虚伪外衣。他只需像鹦鹉学舌般,精准地复述他们前一天讲授的经文片段,再适时地抬起头,用那双清澈(实则空洞)的眼睛望着他们,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点“顿悟”或“崇敬”的神情,偶尔问出一个看似天真实则完全在对方预期之内的问题。这就足够了。
“天才!”神父会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,胡须因兴奋而颤抖,仿佛在贫瘠的矿坑里发现了硕大的钻石。
“此子灵性非凡,必是蒙受主恩!”识字学校的先生捻着稀疏的胡须,向其他孩子夸耀,仿佛阿加普的“聪慧”是他教导有方的铁证。
阿加普内心毫无波澜,甚至想冷笑。看着这些自诩为智慧与信仰守护者的人,因为几句重复的话语、几个预设好的表情就欣喜若狂,像极了得到一颗烂桃子就手舞足蹈的猴子。他们的“珍宝”,不过是他在指尖随意拨弄的廉价玻璃珠。
他站在岸边一块高耸的黑色礁石上,最后一次回望这个被愚昧浸透的村庄。低矮的房屋像一堆被随意丢弃的灰色贝壳,歪歪扭扭地匍匐在海岸线上。教堂破败的尖顶是这片灰暗中最高的存在,却显得摇摇欲坠。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海腥,还有一种更深沉的、由无知和停滞发酵出的陈腐气味。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窒息感。
“离开这里。” 阿加普对着翻涌的、仿佛永无休止的海浪低语,声音被涛声吞没。大陆,那个模糊的轮廓,在他眼中是唯一的光。那里一定有更少的蠢货,有真正的智慧,有能与他匹敌的头脑,有能让他摆脱这令人作呕的愚昧沼泽的空气。他渴望去那里,去证明自己并非这座愚者之岛上孤独的异类,而是属于更广阔、更“文明”世界的一员。他要把这座岛,连同岛上的一切——尤其是那个名为诺德的、愚蠢的污点——彻底抛在身后,永远遗忘在记忆的垃圾堆里。
海风吹拂着他年轻而充满野心的脸庞,带着咸涩的凉意。他转身,不再看那令人厌烦的村庄,目光坚定地投向海平线外那未知的、被他寄予厚望的大陆方向。他并不知道,有些污秽如同海藻的种子,一旦沾染,便深深嵌入灵魂的缝隙,远渡重洋也无法洗净。而那座他急于逃离的、埋葬着“愚者”诺德的山洞深处,那沉闷的、如同巨大心脏搏动般的“敲门声”,早已在无人知晓的维度,叩响了命运扭曲的门扉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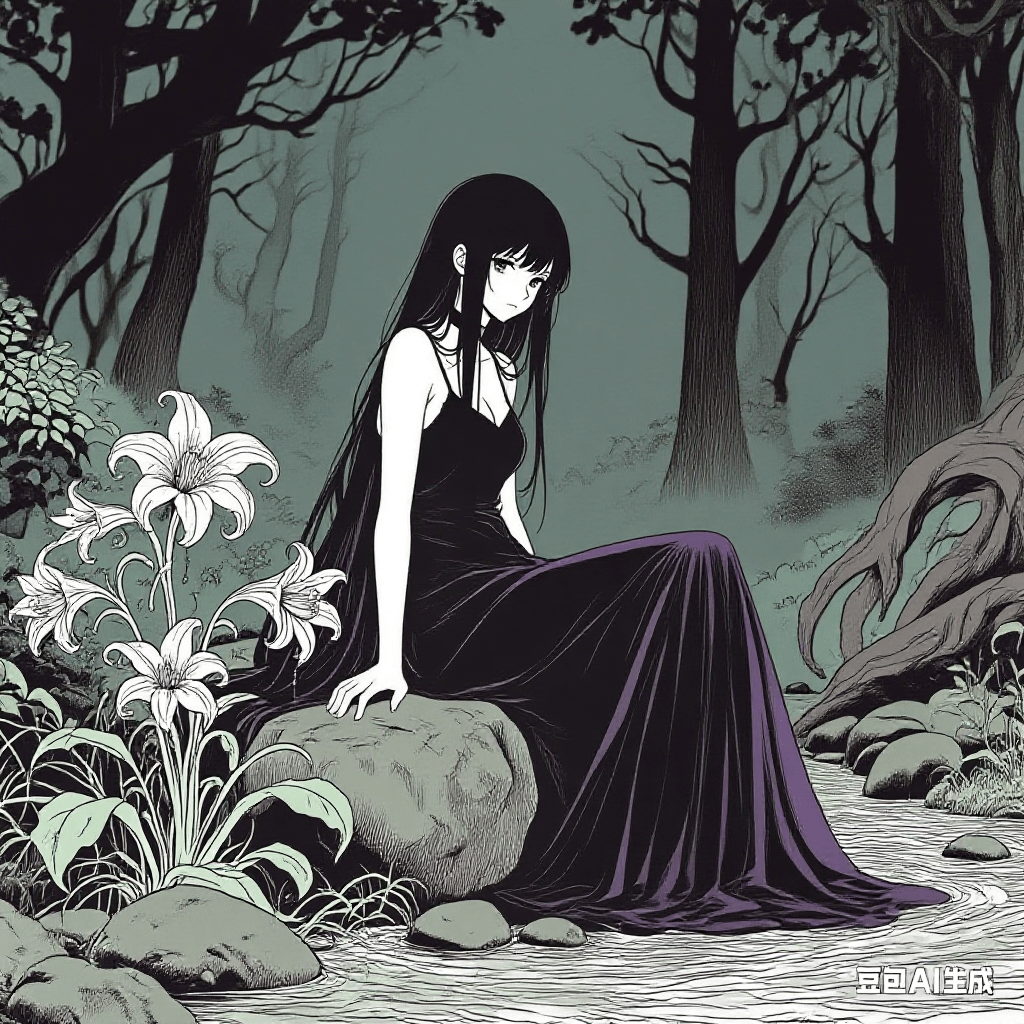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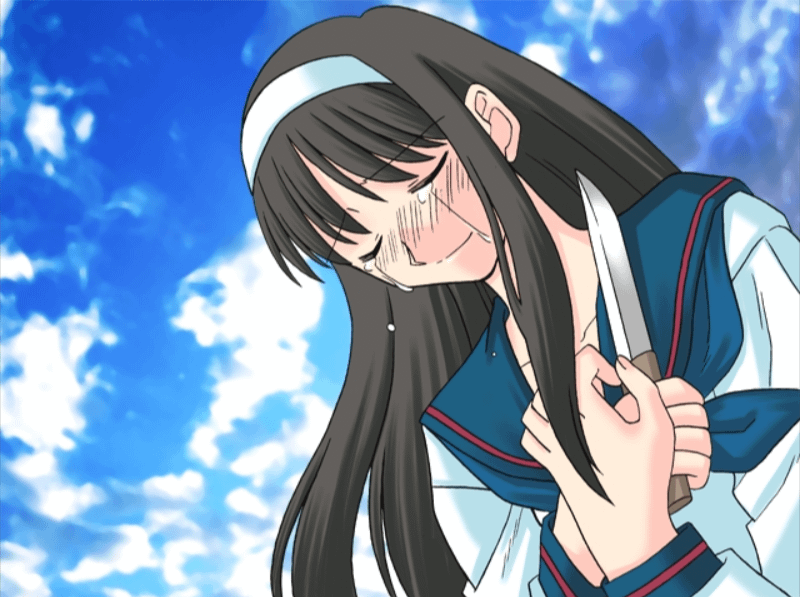

- 最新
- 最热
只看作者